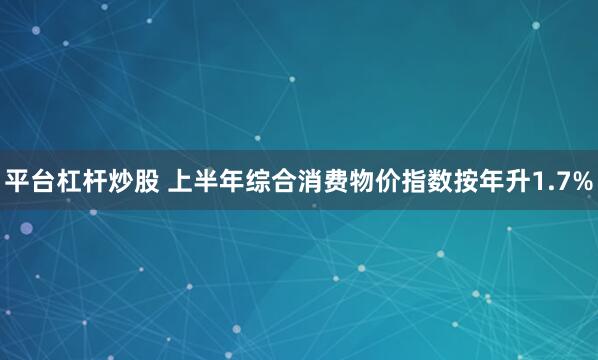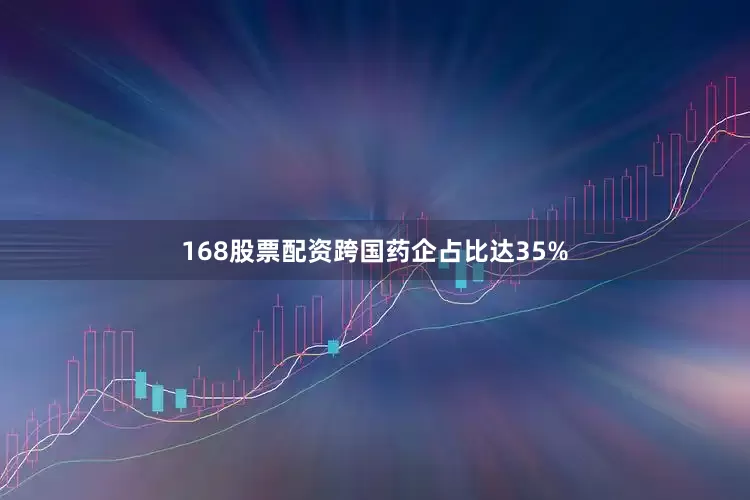01
1948年冬,豫西的旷野上,一场追逐战的硝烟刚刚散去。
风很冷,刮在脸上像刀子。陈赓站在一处高岗上,举着望远镜,沉默地扫视着远方空荡荡的地平线。他的身后,是同样沉默的参谋和警卫员,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出声。
不久前,这里还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巨大陷阱,数万大军潜伏于沟壑与村庄之间,只为等待一个猎物——国民党军张轸兵团。
然而,现在陷阱已经落空。猎物不仅逃脱了,甚至连一根毛都没留下。
「司令,侦察部队回报,张轸兵团主力已于昨夜转向,经泌阳退回南阳,我军再追……已经来不及了。」
一名作战参谋低声报告,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疲惫与懊丧。
陈赓没有回头,望远镜依然稳稳地举着。没有人能看清他此刻的表情,但那紧绷的肩部线条,却透露出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。
良久,他缓缓放下望远镜,呼出一口白气,那白气在严寒中迅速凝结、消散。
「一份电报……」
他的声音很轻,却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,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颤。
「就因为一份电报,我们数万将士在这里挨冻了几天几夜,最后看着敌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。」
他转过身,目光扫过每一位部下的脸。那双曾令无数敌人胆寒的眼睛里,此刻没有怒火,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。
「是我陈赓的疏忽。」
他说完,便大步向山下走去,厚重的军大衣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所有人都能感觉到,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这次失利,不仅是一次战役的挫败,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对于志在经略中原的解放军而言,这是一个不该出现的重大失误。
而对于陈赓个人来说,他敏锐地意识到,这次失误的后果,可能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。
他仿佛已经能感受到,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中野司令部里,那位平日里温文尔雅、极少动怒的司令员——刘伯承,在看到这份战报时,将会是何等失望的表情。
他更不会想到,几乎在同一时间,在另一个战场上,他的老乡兼战友粟裕,正以一场场酣畅淋漓的大胜,将自己的声望推向顶峰。
命运的指针,似乎就在这不经意间,悄然转向。
02
时间拨回到一年多以前的1947年。
解放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华大地,无数将星在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宏大战争中冉冉升起。
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,在一次内部会议上,曾意气风发地做出了一番点评,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
「最近粟裕、陈赓先后脱颖而出,前程远大。」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在场的各位高级将领,加重了语气。
「将与彭、刘、林并肩迈进,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。」
这句评价的分量,重如泰山。
彭德怀、刘伯承、林彪,这三位当时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野战军最高军事主官,是我军最顶尖的统帅。陈毅将粟裕和陈赓与他们并列,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期许与认可。
在座的将领们,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。因为所有人都清楚,无论是以智计百出的指挥艺术,还是以辉煌的战功来看,粟裕和陈赓,都当得起这份赞誉。
尤其是陈赓,在很多人看来,他的综合条件甚至更为优越。
他与粟裕同为湖南老乡,性情却截然不同。粟裕内敛沉静,不善言辞,像一柄藏于鞘中的利剑。而陈赓则外放风趣,机敏过人,走到哪里都能迅速成为焦点。
两人的革命起点,陈赓也要更高。
1927年的南昌起义,那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个战场上并肩作战。当时,20岁的粟裕,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。而24岁的陈赓,已经是战功赫赫的营长。
此后的革命生涯中,两人虽然分属不同的战略方向,却始终保持着齐头并进的态势。
土地革命时期,粟裕在南方艰苦的游击战中磨砺,担任过偏师军团的参谋长。而陈赓则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经受考验,抵达陕北后,成为了红一军团的师长。级别上,两人不相上下。
抗日战争爆发,他们又各自成为一方的支柱。粟裕在新四军,从支队副司令员一路成长为第一师的师长,在苏中地区打出了“七战七捷”的威名。陈赓则在八路军,率领386旅驰骋太行,让日军闻风丧胆,甚至在敌军的装甲车上都涂上了“专打386旅”的标语。
按照当时八路军的“旅”与新四军的“师”大致对等的级别来看,这一时期,两位将星依旧是并驾齐驱,难分伯仲。

因此,当1947年陈毅那番话传出时,几乎所有人都相信,这两位湖南人,必将成为未来解放军最耀眼的双子星。
03
陈毅之所以在那时特别提到陈赓,是有着深刻的战略背景的。
1947年夏,刘邓大军主力如同尖刀,毅然挺进大别山,将战争的火焰直接烧向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。这一行动,极大地震动了南京的蒋介石。
为了策应刘邓主力,也为了在中原这盘大棋上布下更灵活的棋子,中央军委赋予了陈赓兵团一项独立的战略任务。
陈赓与政委谢富治一起,率领麾下的第四纵队、第九纵队以及孔从洲将军率领的起义部队一部,独立经略豫西地区。
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担子,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。
这意味着,陈赓兵团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(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)的直接指挥,成为了一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战略兵团。
陈赓没有辜负这份信任。
他率部在豫西大地纵横驰骋,时而集中兵力猛攻敌之坚城,时而化整为零发动群众,迅速建立起了以伏牛山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。
一时间,豫西战场的捷报频传,搅得国民党军后方大乱,就连坐镇西安的胡宗南也寝食难安。蒋介石更是被陈赓的凌厉攻势所震惊,一度亲自飞抵西安,坐镇督战。
这是陈赓军事生涯中的高光时刻。
他所指挥的部队,兵力雄厚,战绩卓著,俨然已经具备了一个独立野战军的雏形。当时,中央军委内部甚至已经开始酝酿,准备正式成立“鄂豫陕野战军”,并由陈赓出任司令员。
如果这个设想能够成为现实,那么陈赓的地位将瞬间跃升,与彭、刘、林、陈粟等人并列,成为真正的方面军统帅。
然而,历史的走向,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变数。
就在陈赓的声望达到顶峰之际,全国的战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。中央经过审慎的全局考量,最终决定,将战略决战的重心,放在中原地区,准备在这里与国民党军的主力兵团进行一场空前规模的大会战。
战略重心一转移,所有的棋子都必须为大局服务。
于是,“鄂豫陕野战军”的构想被暂时搁置。陈赓兵团也被要求结束在豫西的独立作战,重新归建中原野战军序列,配合主力兵团行动。
机遇,就这样擦肩而过。
与陈赓的“收”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粟裕的“放”。
几乎在同一时期,粟裕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愈发成熟的指挥艺术,赢得了中央的高度信赖。为了让粟裕能够更好地施展拳脚,不受任何掣肘地指挥大兵团作战,中央甚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组织调整——将华野司令员陈毅调往中原,协助刘邓指挥。
史称“陈不离粟”。
这一安排,使得粟裕成为了华东野战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,手握十六个纵队的雄厚兵力,兵强马壮,将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,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一收一放之间,两位将星的轨迹,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分化。
而导致这种分化的原因,除了宏观的战略布局之外,更深层次的,或许还要从陈赓在两次关键战役中的表现说起。
0 G4
第一次,是1947年底的确山之战。
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陷入了国民党军白崇禧部的重重围困,形势岌岌可危。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,像一枚楔子钉在敌人的心脏,但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,部队减员严重,补给断绝,急需外力的支援。
毛泽东的目光,投向了活跃在周边的另外两支大军:陈赓、谢富治兵团,以及陈毅、粟裕率领的华野主力。
如何解大别山之围?
陈赓和粟裕,这两位顶级将领的思路不谋而合。他们同时看上了白崇禧部后方的一个重要据点——确山。
确山,是连接武汉和信阳的咽喉要地,是白崇禧大军的后勤补给中枢。一旦确山失守,白崇禧必然军心大乱,被迫从大别山抽调主力回援。
这,正是兵法中的“围魏救赵”之计。
方案上报中央,毛泽东当即拍板同意。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,就此拉开序幕。
粟裕迅速下令,由华野悍将陈士榘、唐亮率领华野外线兵团(又称“陈唐兵团”),日夜兼程,前去与陈谢兵团会师,共同攻打确山。
一时间,两大野战军的精锐之师,云集确山城下。
确山的守敌,是国民党军的整编第二十师,师长杨干才。这是一支战斗力相当强悍的部队,作风顽强,尤其擅长防守,不久前还曾在藤县重创过华野的一纵和四纵,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
但我军的优势更为明显。
两个兵团加起来,总兵力数倍于敌,并且装备了大量用于攻坚的重武器。从指挥员到普通士兵,所有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信心。
然而,战争的进程,往往会偏离预想的轨道。

05
战役的初期指挥,由陈赓负责。
这既是上级的指定,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安排。毕竟,陈谢兵团对豫西的地形和敌情更为熟悉。
陈赓很快做出了战斗部署。他计划集中优势炮火,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,一举摧毁敌人的防御体系。
然而,就在这个部署中,出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疏漏。
确山城防,主要依托于城外的三个制高点。这三个高地互为犄角,是支撑整个防御体系的骨架。要攻下确山,必须先拔掉这三颗钉子。
陈赓的部署,集中力量攻击了其中的两个制高点,对于第三个,或许是认为可以后续轻松拿下,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正是这个看似微小的疏漏,给了顽强的守军喘息之机。
战斗打响后,我军攻势凌厉,很快就对其中两个高地形成了压倒性优势。但敌人也立刻察觉到了我军的意图,他们迅速将兵力和火力,向仅存的那个未被重点攻击的制高点集中。
战斗,瞬间陷入了胶着。
我军每前进一步,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攻击的速度被严重延缓,速战速决的计划,变成了消耗巨大的攻坚战。
战局迟迟无法打开,上级指挥部开始感到焦虑。在这种情况下,临阵换将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选项。
很快,新的命令下达:战役的统一指挥权,移交给华野的陈士榘。
陈士榘接手指挥后,立刻调整部署,准备发起新一轮的猛攻。但此时,战机已经悄然流逝。
白崇禧并非庸才。在得知确山遭到猛攻后,他一面严令杨干才死守,一面也迅速派出了援军。
虽然白崇禧老谋深算,并没有调动围困大别山的主力,仅仅派了三个师的兵力前来增援,但这对于正在攻坚的我军来说,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。
如果不能在敌援军赶到之前拿下确山,我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。
陈士榘当机立断,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。
确山之战,虎头蛇尾地结束了。
06
战后的复盘,是沉重的。
此役,我军不仅未能攻下确山,给予敌人沉重打击,反而自身蒙受了不小的损失。
更重要的是,战略目标完全落空。
白崇禧派出的援军有限,其主力部队依旧死死地围困着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。“围魏救赵”的设想,最终只成了一厢情愿。
一次任务,两个目标,无一完成。
当然,一场战役的失利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两大野战军的部队首次配合作战,彼此的战术风格、指挥体系都存在差异,协同不顺在所难免。两个兵团地位相当,指挥上存在多头领导的问题,也影响了作战效率。
但是,作为战役初期的总指挥,陈赓无疑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。
那个被忽略的制高点,成为了整个战役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瑕疵。它就像一根鱼刺,卡在了所有人的喉咙里。
这次失利,就像是在陈赓完美的履历上,划下的一道不深却格外显眼的印痕。
它让一些人开始思考:在指挥这种大规模、多兵团协同的复杂战役时,陈赓是否还像他指挥自己的老部队那样得心应手?
疑问的种子,一旦种下,便会悄然生长。
如果说确山之战,还只是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,那么几个月后的另一次失利,则让它长成了一棵无法忽视的树。
07
时间来到1948年初,宛西战役刚刚结束。
在中原战场上,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拉锯战愈发激烈。被我军重创的国民党张轸兵团,在对新野、镇平、内乡一带进行了报复性的“扫荡”之后,迅速收缩兵力,全部退守南阳城,摆出了一副坚壁清野、严防死守的姿态。
与此同时,国民党军的另一支王牌主力,号称“狐狸”的胡琏所率领的兵团,也已经开进到了南阳东北方向的临颍地区。
张轸与胡琏,两部相距不过数百里,互为犄角,给我中原野战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。
如何打破这个僵局,在中原腹地打开新的局面?
中央军委的电报,雪片般地飞向中野司令部。经过反复的研究与权衡,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被制定出来。
这个计划的核心,是“牵牛”与“屠牛”。

所谓“牵牛”,就是以一部兵力,牵制住战斗力更强的胡琏兵团,围而不打,使其无法动弹。
所谓“屠牛”,就是诱使相对较弱的张轸兵团出城来援,然后在运动之中,将其分割包围,彻底歼灭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术,也是我军的拿手好戏。
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,中原野战军组建了东、西两个作战集团。
东集团,由猛将陈锡联统一指挥中野第一、三、六纵队,任务是佯攻胡琏兵团侧翼的确山(又是确山),制造压力,将这只“狐狸”牢牢地拖在原地。
西集团,则由陈赓统一指挥,兵力包括中野第二、四纵队,华野第十纵队,以及桐柏军区和豫陕鄂军区的部分地方部队。他们的任务,就是张开一张大网,等待前来增援的张轸兵团自投罗网,并将其彻底吃掉。
整个计划环环相扣,逻辑严密。一旦成功,不仅能歼灭张轸兵团数万有生力量,还能极大地改善我军在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。
所有的目光,都聚焦在了西线总指挥陈赓的身上。
08
战斗,正如预演般地展开了。
东集团陈锡联部对确山发起了猛烈的佯攻,炮声隆隆,杀声震天,胡琏兵团果然不敢怠慢,急忙收缩部队,全力应对,无暇他顾。
坐镇南阳的张轸,在接到胡琏的求援电报后,果然坐不住了。他自恃兵强马壮,又急于在蒋介石面前表现,立刻下令主力部队倾巢而出,向确山方向增援。
他并不知道,自己正一头扎进陈赓预设的巨大包围圈中。
然而,张轸也并非等闲之辈。他的部队虽然在之前的战役中受挫,但主力尚存,官兵也多为悍勇之徒。
当部队行进到预定区域,发现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时,张轸部并未慌乱。他们迅速收拢队形,组织起了凶猛的反冲锋,一时间,枪炮声响彻原野,双方陷入了激战。
张轸兵团就像一头被困的猛兽,左冲右突,拼死反抗,让我军想要迅速将其歼灭的计划,一再受阻。
陈赓坐镇指挥部,神情凝重。
他深知,战机稍纵即逝。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,一旦胡琏识破我军的佯攻,挥师西进,那西集团将面临被内外夹击的巨大风险。
出于稳妥起见,陈赓一面指挥部队加强攻势,一面迅速向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发去电报,请求支援。
刘伯承当即回复,同意了陈赓的请求。中野司令部立刻调动其他主力部队,星夜兼程,向战场赶来。
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。只要援军一到,张轸兵团便插翅难飞。届时,聚而歼之,中原战局将豁然开朗。
然而,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,被围困的张轸,耍了一个狡猾至极的花招。
这个花招,不仅让他成功逃出生天,也让陈赓遭遇了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败。
09
张轸非常清楚,他的兵团指挥部与外界进行联络的无线电台,肯定已经被解放军所监控。他发出的每一份电报,都会被对方截获并破译。
于是,他将计就计,导演了一出精彩的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。
他命令报务员,向驻守信阳的国民党友军发去一份“紧急”电报。电报的内容大意是:我部已陷入共军重围,但仍将继续向东突进,与胡琏兵团会合,伺机从东面突围。
这份电报,语气急切,内容“真实”,充满了决一死战的悲壮。
正如张轸所料,这份电报很快就被陈赓的指挥部截获。
当译电员将电报内容送到陈赓面前时,他几乎没有怀疑。因为这份电报所描述的情况,与战场上的态势完全吻合。张轸兵团确实在拼命向东冲击,这看起来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。
陈赓的脑海里,迅速浮现出了新的战场态势图。
中野的增援部队,正是从东面赶来。如果张轸兵团继续一意孤行地向东突围,那么他们正好会一头撞上我军的援兵。
到那时,自己只需要率领西集团的主力,从后面兜住敌人的屁股,就能轻松地将张轸兵团包了饺子。
一个念头,在他的脑海中闪过。
既然敌人还要继续往东送死,那么自己部署在东面口袋底的部队,就没有必要再和敌人硬拼了。那里,正是我军第四纵队的位置。
第四纵队,前身是八路军的386旅,是陈赓一手带出来的老部队,堪称他的心头肉。在之前的战斗中,四纵已经承担了巨大的压力,伤亡不小。
既然战局已定,何必再让自己的老底子,付出不必要的伤亡呢?
这个想法,充满了“爱兵如子”的温情,也充满了战术上的“合理性”。
于是,陈赓下达了一道足以让他抱憾终身的命令。

「命令,第四纵队,撤出东面阵地,向侧翼转移,收拢部队,准备参与最后的总攻。」
10
军令如山。
接到命令的第四纵队,虽然有些疑惑,但还是迅速地撤离了经营多日的阵地,在夜色的掩护下,悄悄地向一旁转移。
他们留下的,是一个巨大的、致命的缺口。
而包围圈中的张轸,在发出那封假电报后,一直在紧张地等待着。当他派出的侦察兵回报,解放军在东面的包围圈出现松动时,他知道,自己的计策成功了。
他立刻下令,部队先是虚晃一枪,继续向东猛冲了一段距离,彻底麻痹了我军。
然后,在某个时刻,整个兵团突然调转方向,如同一股决堤的洪水,从第四纵队撤离后留下的那个缺口,疯狂地向西涌去,头也不回地逃回了南阳老巢。
等到陈赓发现上当时,一切都已经晚了。
东面的防线已经洞开,西面的部队距离又远,再想追击,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。
煮熟的鸭子,就这么飞了。
一场策划周密、志在必得的歼灭战,最终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目送。
消息传到中野司令部,一向以儒将形象示人、极少发火的刘伯承,罕见地动了怒。
他没有长篇大论地批评,只是在给陈赓的回电中,写下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。
这句批评,不仅仅是针对这次战役的失误,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赓指挥风格中,一个潜在的、也是致命的问题。
这句批评,也让远在中央的毛泽东,对这位爱将的特点,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。
究竟是怎样的一句话,让陈赓黯然神伤,又在冥冥之中,影响了他与粟裕未来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?那封来自刘伯承,措辞严厉的电报,在当时的将领中,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原委,它揭示了一个统帅在关键时刻,最不能动摇的原则……
11
刘伯承在电报中批评陈赓麾下的部队:
「顾虑自己部分的伤亡。」
这短短九个字,对于任何一位爱惜荣誉的将领来说,都无异于一记重锤。它批评的已经不是战术层面的疏忽,而是上升到了指挥员的本位主义思想。
在刘伯承看来,为了全歼张轸兵团这个大的战略目标,任何参战部队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,哪怕是拼光了,也在所不惜。
而陈赓在最后关头,为了保存自己的老部队第四纵队,主动撤销了关键位置的防守,这在刘伯承看来,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。
这种“顾虑自己部分伤亡”的思想,往小了说,是缺乏大局观;往大了说,就是一种变相的“军阀作风”,是人民军队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这次严厉的批评,深深地刺痛了陈赓。
他是一个何等骄傲的人,从黄埔军校到尸山血海的战场,他的人生字典里,很少有“失败”和“指责”这样的字眼。
但这一次,他无话可说。
因为刘伯承说得对。他的确是出于私心,想要保全部队的实力,结果却因小失大,葬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。
这件事,成为了陈赓军事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它让最高决策层意识到,陈赓虽然勇猛善战,机智过人,但在驾驭关乎全局的大兵团决战时,他的思维模式中,似乎还残留着一些“山头主义”的惯性。
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,太看重自己一手拉扯起来的部队。这种情感,在平时是凝聚部队战斗力的优点,但在关键时刻,却可能成为影响战略决策的致命弱点。
12
与陈赓的这次重大失利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粟裕在同一时期的大放异彩。
如果说陈赓的指挥风格是“稳”中带“巧”,那么粟裕的风格就是“险”中求“胜”。
在粟裕的作战计划中,几乎看不到任何瞻前顾后、患得患失的痕迹。他的眼中只有一个目标: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标,他敢于将自己的指挥部,设置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公里的地方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标,他敢于违抗上级的命令,提出更大胆、更冒险、但收益也更高的作战方案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标,他敢于把自己的主力部队,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最危险、最残酷的战场上,哪怕付出巨大的伤亡,也在所不惜。
豫东战役,他敢于在国民党军几个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穿插,上演了一出“中心开花”的绝妙好戏,一举攻克开封,歼敌九万余人。
济南战役,他敢于将主力用于攻城,同时只用少数部队阻击数量庞大的敌援军,最终硬是啃下了这座坚城。

这种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大心脏和“一切为了胜利”的纯粹性,正是作为一名战区统帅,最宝贵的品质。
对于最高统帅毛泽东而言,他需要的,正是在关乎国运的决战中,能够放下一切私心杂念,坚决执行战略意图,敢于冒险、敢于胜利的将领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粟裕无疑是更符合要求的人选。
于是,当天平开始倾斜后,资源的配置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
中央给予了粟裕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支持,华东野战军的指挥大权被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中。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,粟裕更是以中野、华野两大野战军前线总指挥的身份,指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。
而陈赓,虽然依旧是中原野战军中一员不可或缺的悍将,但他所指挥的,始终只是一个兵团。
从方面军统帅的潜在人选,到野战军麾下的兵团司令。
仅仅一年多的时间,两位将星的差距,就这样被迅速地拉开了。
13
当然,用一两次战役的成败,来评判一位将领的全部,是片面的。
战争,本身就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。
陈赓在确山和宛西的失利,固然有他自身指挥的原因,但也与战场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密不可分。
而陈赓的综合能力,也绝不仅仅体现在野战指挥上。
解放战争结束后,当战火蔓延到朝鲜半岛,陈赓再次临危受命,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,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。
在朝鲜战场上,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组织协调能力,尤其是在后勤保障和多国部队协同作战方面,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回国后,他又被委以重任,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,也就是著名的“哈军工”。
他脱下戎装,拿起教鞭,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,培养了第一代宝贵的顶尖人才。从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,到后来各大军工领域的领军人物,无数都出自他的门下。
从这个角度看,陈赓的人生,同样是波澜壮阔,功勋卓著的。
只是,命运就是如此奇妙。
在那个决定谁能成为方面军统帅的关键窗口期,他因为两次不算致命、却足以引起警惕的失误,与那个更高的位置,擦肩而过。
14
历史无法假设。
我们无法知道,如果当初“鄂豫陕野战军”成功建立,陈赓成为第五大野战军的司令员,中国的解放战争史,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。
我们也无法断言,如果陈赓在确山和宛西,选择了更决绝、更不计代价的打法,他是否就能牢牢把握住那次机遇。
我们唯一能看到的,是两位风格迥异的将领,在历史的洪流中,走出了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。
粟裕,将自己的一生,都献给了战争艺术的极致追求。他像一位孤独的棋手,毕生都在思考着如何以最小的代价,获取最大的胜利。他的一生,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战争史诗。
陈赓,则更像一位多才多艺的开拓者。他既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,也能在谈判桌上纵横捭阖,还能在和平建设时期,为国家的未来奠定基石。他的人生,充满了丰富多彩的传奇。
他们两人,最终都在1955年,被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,位列十位大将之中。
这或许是历史给予这两位杰出军人,最公正的评价。
他们的道路虽然不同,但他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,同样不朽。
多年以后,当陈赓与粟裕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再次相遇,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视一笑,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。
过往的那些战火硝烟,那些成功与失落,那些荣耀与遗憾,或许都已在那一笑和一握中,化作了过眼云烟。
他们共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,这本身,或许就已超越了所有的军衔与职位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《陈赓传》 当代中国出版社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 解放军出版社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》《决战:中原解放战争》 军事科学出版社王树增 《解放战争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股票开通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正规杠杆炒股平台作为一个带着两娃的普通家庭
- 下一篇:没有了